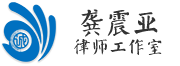“童言无忌”的俗语,道出了人们对未成年人言语真实性的朴素认知——年龄越小,似乎越能摆脱成人世界的功利与虚伪,其表达更接近纯粹的事实。然而在诉讼领域,尤其是刑事诉讼中,未成年人的证言效力却与年龄呈现“反向关联”:年幼者的陈述往往需要更严格的审查,甚至在未达到法定年龄时难以作为独立证据被采信。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,背后蕴含着证据法对真实性、可靠性的深层考量。
刑事诉讼的核心目标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,而证据作为事实认定的基石,必须满足真实性、关联性与合法性的要求。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与表达能力,直接影响其证言的可靠性,这正是法律对未成年人证言设置年龄门槛的根本原因。
从认知规律来看,婴幼儿的大脑发育尚未成熟,对事物的观察、记忆与判断能力存在天然局限。他们可能无法准确区分“想象”与“现实”,容易将听到的故事、梦境与真实经历混淆;对时间、地点等关键要素的感知也较为模糊,难以清晰描述事件的来龙去脉。例如,幼童可能因害怕惩罚而将他人的行为归为自己所见,或因成年人的引导性提问而改变陈述内容。这种认知上的局限性,使得其证言的真实性难以保障。
从意志独立性来看,低龄未成年人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。在家庭纠纷、校园事件等案件中,他们可能因父母、老师的权威压力,或对“听话”的本能顺从,作出迎合成年人期待的陈述,而非客观事实。刑事诉讼中,案件往往涉及激烈的利益冲突,未成年人更可能成为各方影响的对象,其陈述的“自愿性”与“客观性”面临严峻挑战。法律对年龄的要求,本质上是通过预设一个“认知成熟度底线”,筛选出具备基本独立判断能力的陈述者。
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未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作证的最低年龄,但司法实践中,通常会结合未成年人的年龄、智力状况、表达能力等综合判断其证言的证明力。对于年幼、无法正确表达的未成年人,其陈述一般不作为证据使用;对于已满一定年龄(如10周岁以上)、能够清晰表达且认知能力符合要求的未成年人,其证言经法庭质证并结合其他证据印证后,可以作为定案依据。这种弹性处理方式,既尊重了未成年人的作证权利,又通过“补强证据规则”确保了事实认定的准确性。
值得注意的是,法律对未成年人证言的审慎态度,并非否定“童言无忌”的价值,而是在诉讼语境下对“真实”的严格坚守。刑事诉讼涉及对公民生命、自由、财产的剥夺,必须以最可靠的证据为基础。当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不足以支撑证言的可靠性时,法律的“限制”实则是对司法公正的保障——避免因错误采信证言而导致冤假错案,既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,也避免未成年人因卷入复杂诉讼而承受不必要的心理压力。
从更深层的角度看,这种“反向关联”体现了法律对人性的深刻洞察。“童言无忌”的可贵,在于其不受世俗污染的纯粹;而诉讼证据的采信,需要的是经得住理性检验的可靠。前者是生活经验的感性总结,后者是司法规律的理性提炼。当二者相遇时,法律选择以年龄为标尺,在保护未成年人与维护司法公正之间寻找平衡,既不苛求年幼者承担超出其能力的证明责任,也不轻易将未经检验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。
因此,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人证言的年龄要求,并非对“童言无忌”的否定,而是证据法科学性的体现。它提醒我们,在追求事实真相的过程中,既要尊重不同主体的表达权利,更要以专业的标准审视证据的可靠性,唯有如此,才能让每一份判决都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,实现法律的公正与威严。
【龚震亚律师,上海刑事辩护律师,电话18301725408】回到首页